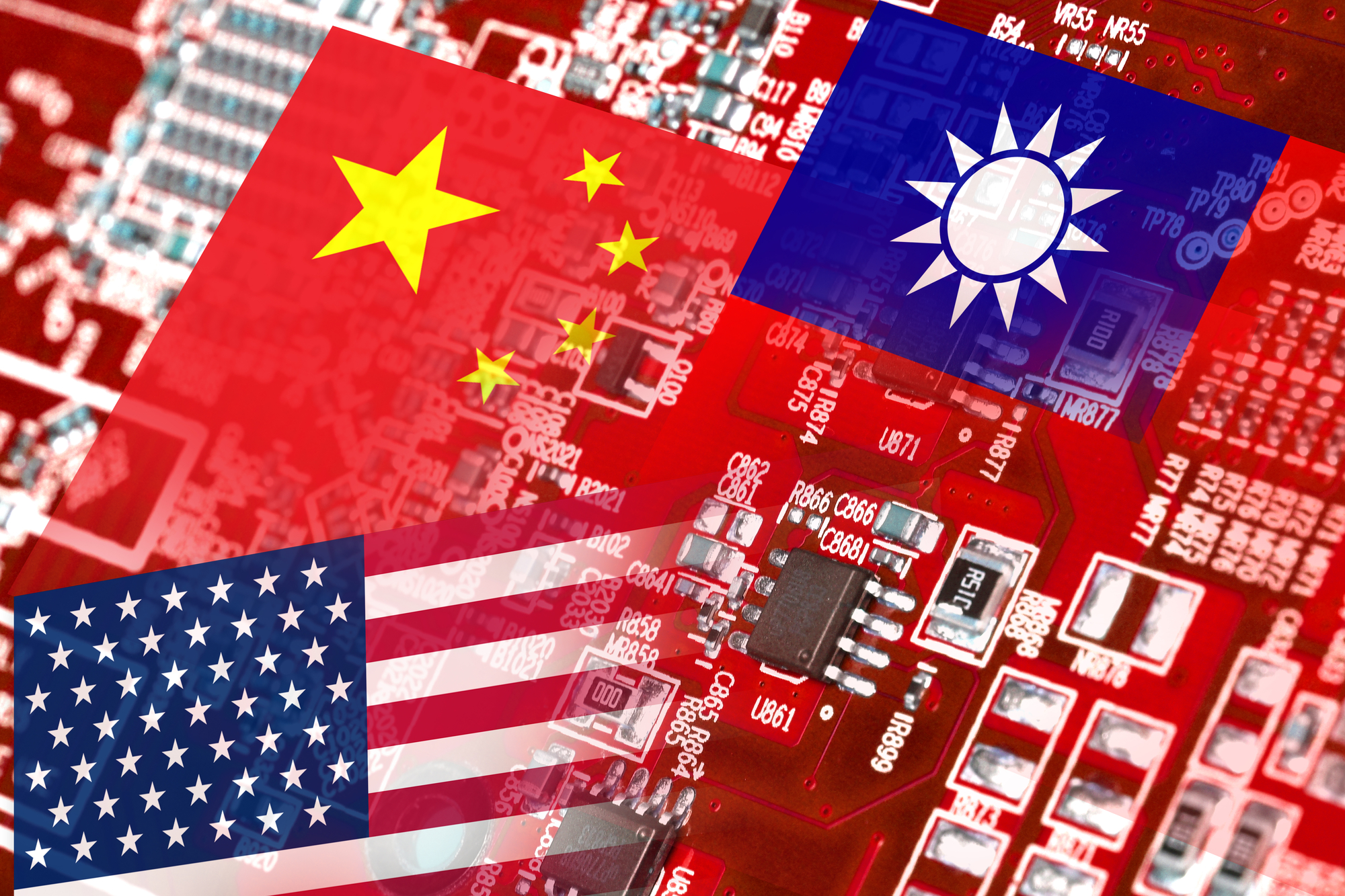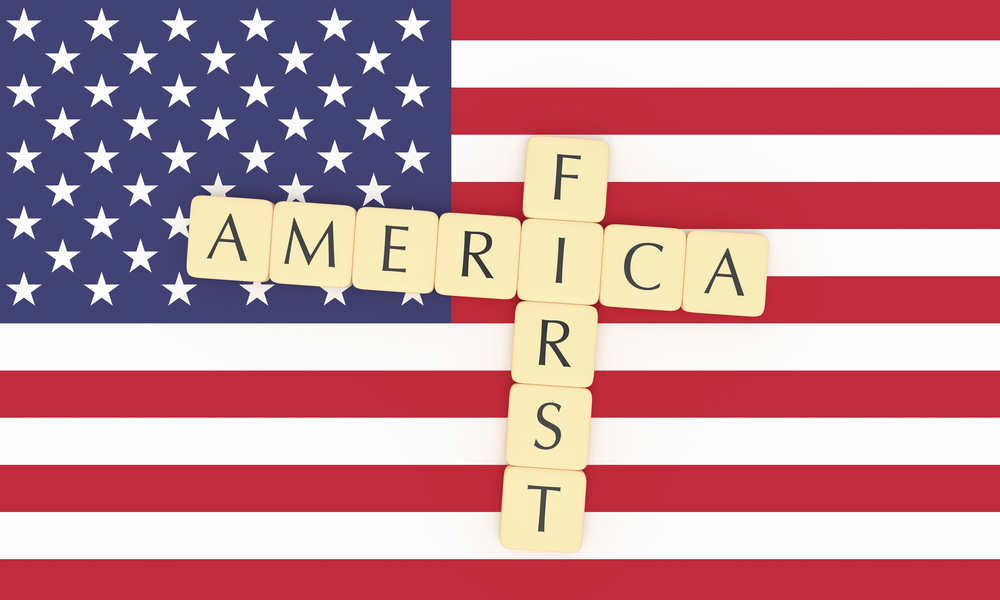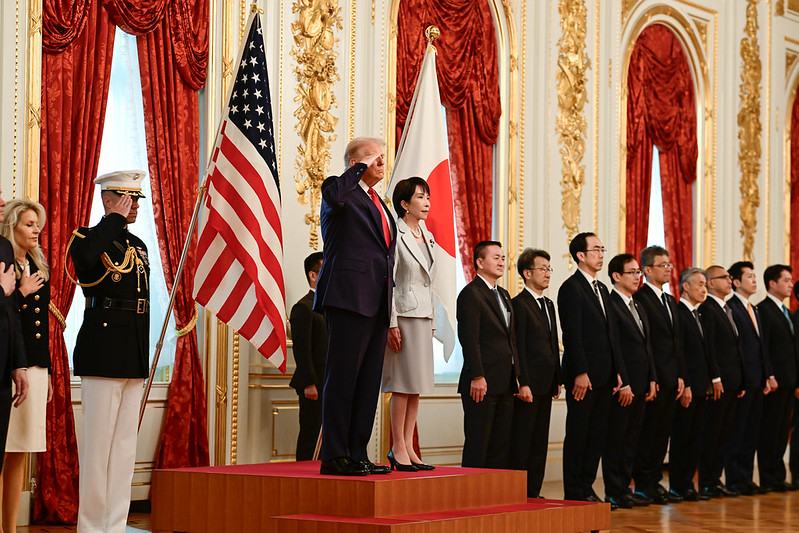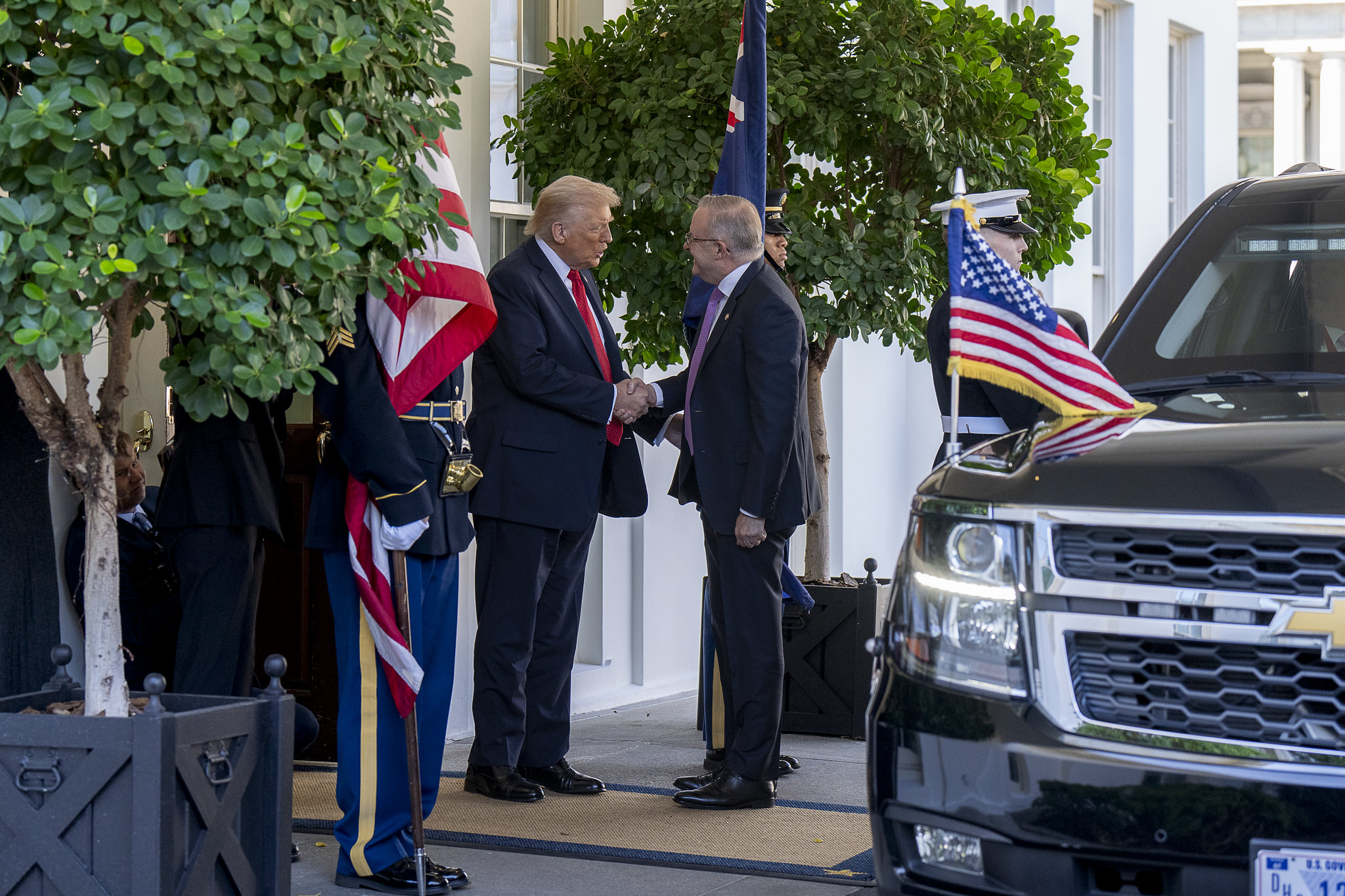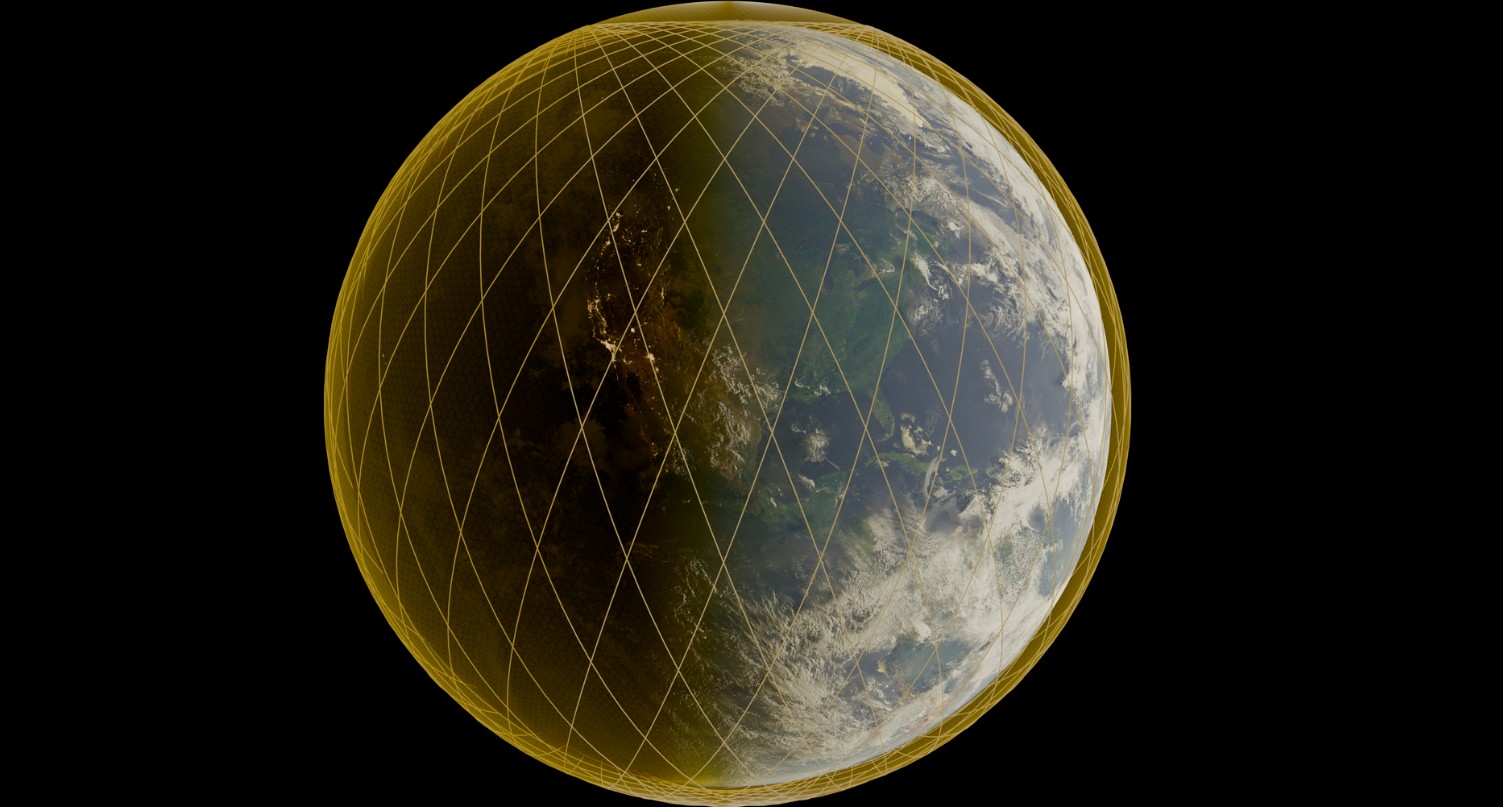2021年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強森,以及澳洲總理莫里森發布聯合聲明,宣告成立AUKUS。(圖片來源:https://vienna.usmission.gov/trilateral-aukus-statement-iaea-bog-nov-2021/)
美國聯盟管理新模式的誕生?
丁樹範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2021年9月1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以及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發布聯合聲明,宣告成立AUKUS。當時,世人注意的焦點是三國將合作為澳洲研製八艘核動力傳統武力潛艇。
隨著三國討論越來越密集時,AUKUS合作的內容擴及到新興技術的合作,使得AUKUS形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Pillar I)是三國合作研製澳洲需要的核動力潛艇。第二部分(Pillar II)則是著重六大新興技術,包括人工智慧、量子技術、水下能力、網路空間、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電子戰,以及兩個功能性論壇:創新和資訊分享。AUKUS上述的安排可能使得自冷戰以來美國建立聯盟(alliance)體系的管理帶來變化,而形成新模式。
關於「聯盟」的幾個核心問題
聯盟是指兩國之間,或兩國以上國家之間簽訂正式安全條約,當一方被攻擊時,視為是對簽約另一方的攻擊,另一方有義務對被攻擊方提供援助。所以,聯盟的出現是因為存在著強大的敵人,聯盟簽約的成員國企圖以集體力量對抗可能的侵略。
這是冷戰時期在歐洲出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原因:蘇聯可能有野心進行共產主義擴張。蘇聯可能的擴張造成歐洲國家的恐慌和顧慮,轉而尋求透過建立聯盟發展出集體安全,並以美國為首建立聯盟體系。美國則在此聯盟體系建立管理模式,進而規範彼此的權利和義務。這種管理模式建立的基礎是對蘇聯可能侵略的恐懼,誘因則是提供集體的安全保障,使得聯盟成員得以保持主權獨立自主而不被侵略。
然而,冷戰結束和蘇聯瓦解使得美國建立的聯盟體系受到衝擊。核心的問題是聯盟是否有存在必要,以及如果仍需要,其功能如何定位?與之相關的議題是:美國能提供什麼誘因使得聯盟成員仍接受美國的領導和管理?這是2019年7月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曾批判北約正在腦死的背景。
進入全球化時代更加重人們對聯盟的質疑。誇張地說,全球化強調經濟和商業利益,甚至,企業利益重於安全。特別是當中國和俄羅斯的經濟整合到西方的經濟體系時,再加上非傳統安全論述的發展,美國如何維持住聯盟體系是很大的挑戰。
習近平執政是轉變的開始。習近平的咄咄逼人和具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再加上俄羅斯明目張膽地侵略烏克蘭,以及中國支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使得美國的聯盟體系得以復甦,因為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必須再借重聯盟概念以因應中國和俄羅斯越趨發展的侵略性。
美國向盟友提出的誘因
然而,部分美國盟友對美國未來發展有諸多疑慮,這特別是經歷川普(Donald Trump)執政的疑慮。AUKUS或類似安排的出現,某種程度成為美國提供盟友的誘因,使美國為主的聯盟體系得以維持。
這特別是指AUKUS的第二支柱(Pillar II)。這些新興技術涉及各國未來經濟、技術,甚至整體國力的發展。而美國在這些新興技術領域都佔有領先地位。如果透過類似AUKUS的安排,長期而言對相關加入國家未來的經濟、技術,以及整體國力發展必然有很大的助益。這可以解釋為何有很多國家期待加入AUKUS。
另一個安排是美國國防部正在推動的「印太產業韌性夥伴」倡議(Partnership for Indo-Pacific Industrial Resilience, PIPIR)。其特點是利用印太各國獨特的產業利基,美國和域內國家透過共同發展和共同生產等方式,處理共同武器獲得或後勤持續等國防議題。
其可能結果是,相關參與「印太產業韌性夥伴」倡議國家的生產或技術發展水準可透過此倡議而提升,進而帶動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商業利益。從某個角度而言,也可以增強相關國家的國防和軍事實力,達成國家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
某種程度而言,這是美國向盟友提出的一種誘因,使聯盟體系得以維持。同時,透過包括軍事在內的能力建設,也可以間接達成嚇阻中國侵略行為的政治目標。這是聯盟管理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