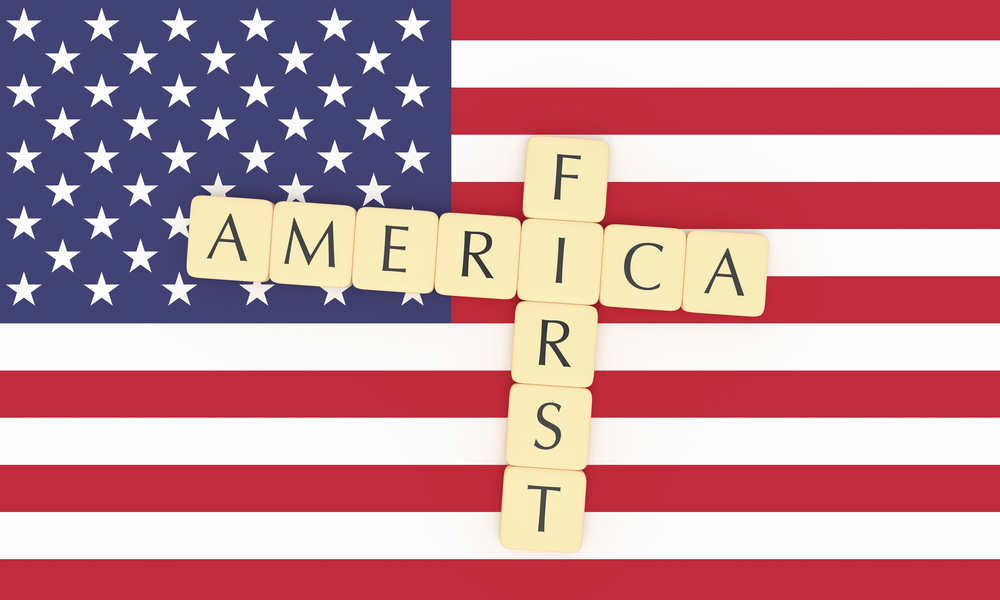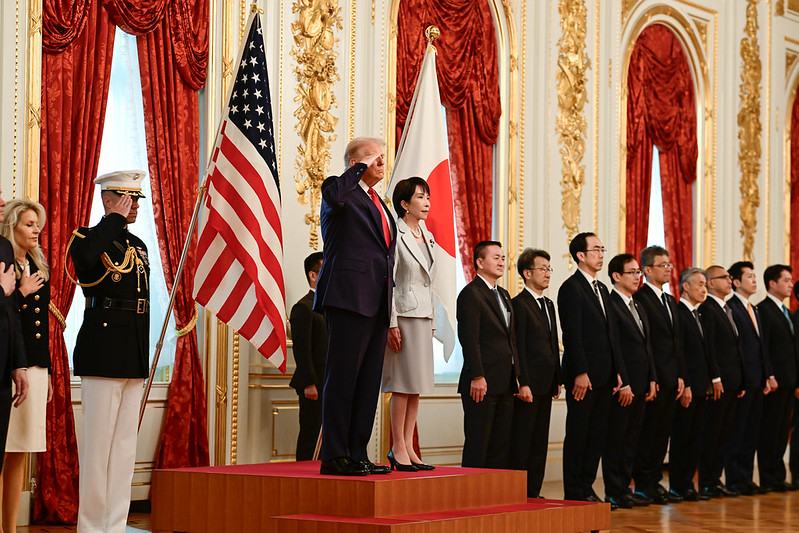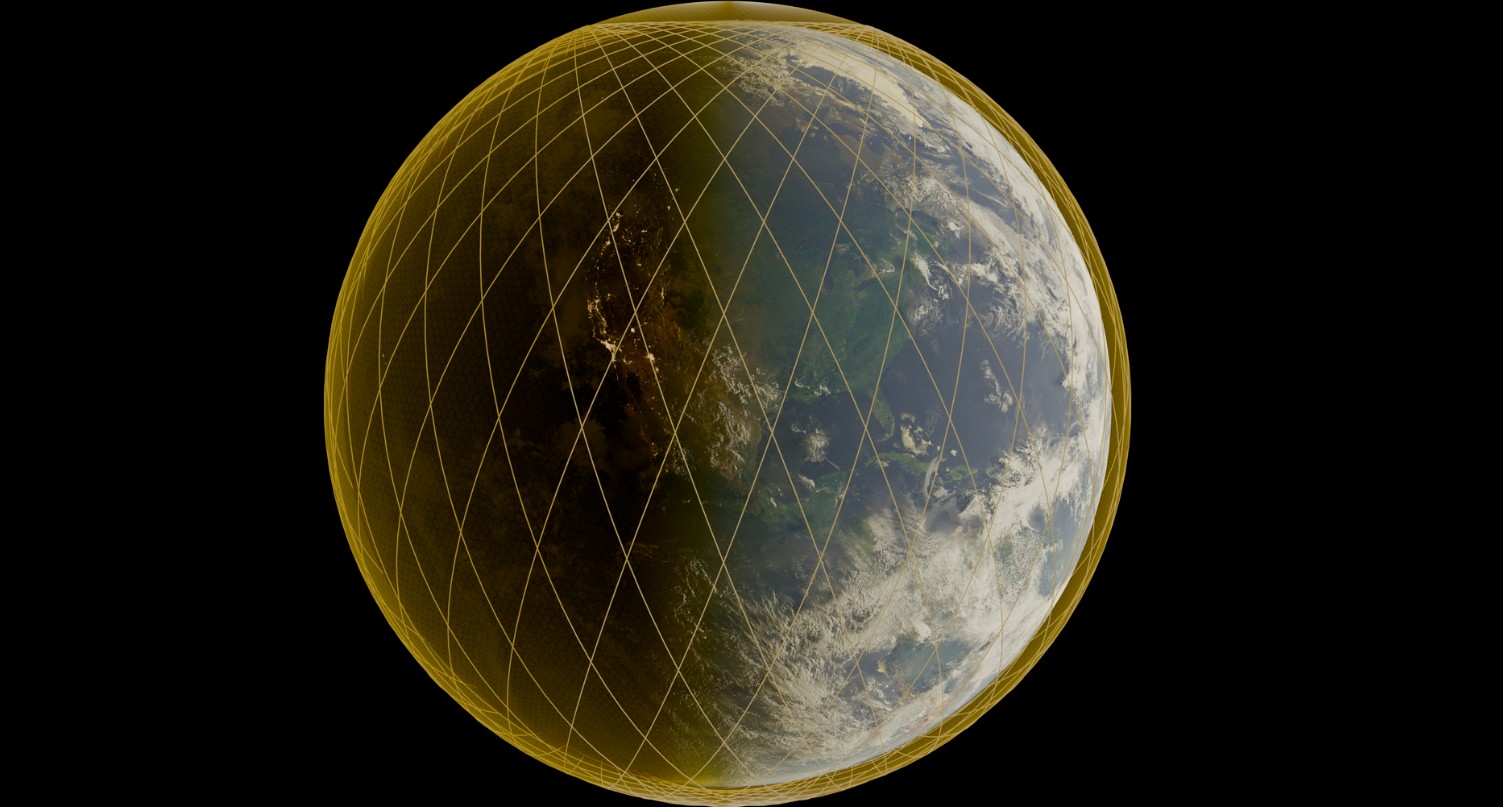2025年1月再次任職美國總統後,川普以極短的時間重啟並升級他在第一任期的「攻勢性貿易政策」。
(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whitehouse/54421119077/in/album-72177720324774955)
獨行其道,亂序天下:
川普關稅攻勢再起與WTO多邊貿易的衰落
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2025年1月再次任職美國總統後,川普(Donald Trump)以極短的時間重啟並升級他在第一任期的「攻勢性貿易政策」,特別是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貨品。此一政策的特徵有二:一是違反美國在WTO所承諾之拘束稅率,二是援引國家安全作為其政策背後的主要考量。由於這樣的關稅政策導致很多國家的經濟利益受損,甚至也造成美國境內諸多消費者的民生負擔,於是目前無論國際或國內皆引起廣泛的反彈聲浪。
然而,川普或許多少有幾分瘋狂,但絕對不是一個非理性決策者。他提高外國產品進口關稅的核心邏輯,實非僅僅出於「保護美國勞工」的政治修辭或競選承諾,而是有意識地在重構全球供應鏈與改進美國財政自救機制。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川普2.0的關稅政策宜被理解成一種「地緣財政」的經濟治國術(statecraft),旨在對抗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國際影響力、減緩美元作為全球通貨所造成之經常帳赤字持續化和本土產業競爭力的空洞化。
從匯率政策的角度來看,川普是以貿易關稅作為槓桿,壓制貿易夥伴國(特別是對美出超的國家)之出口競爭力,以此支撐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從而使得美國境內的通膨情況被維持在一個相對可控的局面,如此才能確保金融資本對美國資產的信心。所以,川普的關稅政策不是只有貿易效果的行政措施,而是同時融合金融、貨幣及國家競爭力的多層次戰略。
此外,川普也意識到美國對外貿易的失衡(進口大於出口)與國債規模膨脹之間的連結性。如果美國繼續仰賴中國(或其它國家)購買美債,美國的貨幣主權就會持續弱化,而這樣的弱化將導致美國在與中國競爭全球影響力的時候面臨劣勢。準此,川普選擇直接加徵進口關稅的粗糙手法,使企業「回流本土」或「移到美國」,作為刺激和重建美國製造業的動力,並在過程中盡可能降低對外國資金之依賴,從而改善美元流動性壓力,並提高美國人民就業機會。
強權作為國際建制運作之核心推力
值得吾人思考的是,川普的關稅政策直接挑戰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核心規範,也就是以「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兩大原則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建制(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從川普或白宮發言人在公開場合上的說詞內容可推知,美國現在期待它的貿易夥伴國個別來找美國協商,用「雙邊談判」模式來商定接下來(至少四年)的貿易互動,而不是繼續留在多邊主義架構下的WTO。此種戰略布局反映出美國作為全球霸權的能耐,也就是憑一己之力就對行之有年的多邊國際規則進行強勢干擾。此舉雖然和新自由制度主義關於國際合作的論點明顯衝突,卻也同時讓吾人有機會反思,昔日大力推動和支持WTO成立與運作的美國可以因為多邊國際貿易建制不再能滿足其國家利益,就翻臉不認人。簡言之,國際合作得靠強權的支持和參與;國際建制若是發揮了作用並不是因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解釋正確,而是因為建制或制度的幕後有龐大權力為其撐腰。
因此,如果世人或多數國家不滿川普政府現在囂張跋扈的單邊行徑,就必須設法找到另一個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權出來主持國際貿易大局,填補美國留下之權力真空。歐盟(European Union)和北京當局是最有可能性及資格的兩個行為者,但前者似乎沒有意願或意願不強,而後者雖然有意為之,卻難為眾國所信服。正因為如此,川普才有把握有空間能恣意而為,且態勢十分高傲;毋寧,國際社會或許不悅於一個自私自利的川普,但還未達到捨得放下美國轉身投靠新主的程度。
高關稅政策引發的國際經濟連鎖反應
俗話說,鑑往知來。川普在其第一任總統就職期間施行的貿易關稅政策中已揭示他政策的核心目標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換言之,川普既想再次振興美國製造業,也想達成對北京制衡的戰略目標。職是之故,美國運用《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與《貿易法》第301條作為合理化自身行為的基礎,將中國視為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之來源,從而進行大規模的課稅。此種情況未隨著民主黨的拜登(Joe Biden)上臺有所變化,反而是川規拜隨又持續了四年,如今隨著川普再次回鍋執政,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產品進一步課徵高達145%的關稅。對此,北京當局報復性地課徵125%的關稅來回敬,雙方一來一往之際,引發多國通膨與金融市場波動,美國自己似乎也在相當程度上開始自食其果,美債殖利率急升但價格暴跌(4月21日前後的市場變化),同時美元開始連續性貶值。這些變化皆間接暗示經濟蕭條的風雨欲來。但對川普來說,強勢的美元不利該國產品在全球貿易市場的競爭力,為了振興美國的製造業,他不惜干犯眾怒地執行「弱美元政策」。
回顧1816年以降的六次美國經濟不景氣,其中高達五次皆與關稅有所關聯。毋寧,當華府的決策者傾向用單邊模式啟動關稅政策時,尾隨而來的就是國際貿易秩序失衡、外資抽離美國、企業主信心崩潰與金融資產泡沫化,其衝擊深遠且短時間難以逆轉。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川普的關稅政策破壞的不僅是美國與其貿易夥伴的商品流動、合作信任,更是重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結構。此結構一旦遭到破壞,國際交易市場上的信用、穩定性和不歧視原則就會嚴重地邊緣化;美國或許仍能在相對比較的基準上依舊成為「獲利者」,但本身的國內經濟將付出一定的代價,甚至重演1837年、1893年或1930年的慘況。